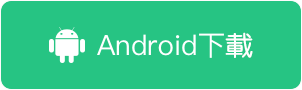一臉的驚愕,雖然如今腦子一片空白,可女子卻沒來由地覺得,自己絕不該是這般樣貌……
老桂家的這時走上前,從妝檯上拿過一把篦子,笑道:「我給姑娘梳梳頭吧,錢婆子搜刮半天,到底抱不走這最值錢的,這妝檯可是宮制,大爺得來之後,直接叫搬到姑娘這屋裡,可不讓西頭的眼饞壞了,許是那時候,便生出了壞水。」
女子看向老桂家的,疑惑「西頭的」,或是那位什麼三夫人。
身後有腳步聲響起,原來是阿英蹦蹦跳跳地跑了進來,手裡趿着一雙土布的女人鞋子,臉上全是喜色。
「娘,我回來了!」阿英笑呵呵地叫了一聲,便將鞋遞給了老桂家的。
老桂家的讓女子在妝凳上坐了,替她穿上了鞋,不由笑道:「姑娘腳小,只有貴人家女孩才這般,先湊合吧,回頭我幫你做新的!」
說完,老桂家的回頭看看女兒,笑問:
「莫不是黑燈瞎火拾到金子了,瞧把你樂的。」
「剛才我回灶房,個個都在忙活,上去一打聽,原來大爺回來了,」
阿英樂呵呵地道:
「這下平姑娘算是得救,或是用不着嫁給那花舅爺了。」
女子看向阿英,腦子又糊塗起來,到底她是大爺的通房,還得着這紫檀妝檯,怎轉眼就被逼嫁給那什麼花舅爺,三夫人並非主母,為何這般膽大?
「姑娘,想個法兒,趕緊去求大爺?」阿英在旁提議道。
老桂家的猶豫了一下道:「姑娘,您自個兒端量着吧,花舅爺素沒有好名聲,吃喝嫖賭樣樣齊全,靠着三夫人撐腰,在府里真當自個主子一樣,先頭他娶過幾個妻妾,最後都被他搓磨死了,有一位據說被花舅爺拿棍子生生打死,平姑娘要嫁過去,怕是……不好!」
女子不自覺地抖了一抖,心已經沉到了谷底。
「這可如何是好?」阿英在旁邊着急起來。
「事在人為,」老桂家的扶着女子坐回到床上:「或是這事兒……得求大爺給個說法,虧得大爺已然回府,倒未必沒有機會。」
女子瞧着母女二人,不由苦笑起來,如今在這府里,她是兩眼一抹黑,大爺在哪個地兒待着,她自是不知道,怕是就算大爺到了跟前,她也必認得出來。
畢竟夜深,阿英歲數小,熬不得夜,沒一會便困到不行,老桂家的只得告辭,帶着女兒離開了歲蕪院。
一時,女子獨自躺在床上,竟是腦子亂成一團,想來想去,只覺入了絕境。
想到最後,女子竟睡了過去……
「平姑娘,良辰吉時,還不趕緊起來。」屋外一陣尖利叫聲,把女子一下子驚醒過來。
門猛地被人從外推開,進來的是那婆子,身後還跟了兩個婆子模樣的,瞧着手上似乎捧着什麼。
「趕緊着,迎親的人已經在東邊角門等着了,」
錢婆子徑直上前,將正坐在床邊發愣的女子一扯:
「愣着做甚,今日平姑娘大喜,還不梳洗裝扮上!」
話雖說得好聽,錢婆子和那倆婆子手腳卻不客氣,一擁上前,有人拉胳膊,有人按脖子,三下五除二,將一件紅彤彤的嫁衣,往女子身上套去。
原本還有些迷糊的女子,一下子清醒過來,開始拼命掙扎:「別碰我!」
三個婆子皆是體粗力壯之人,對付個年輕女子,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沒一時,那身嫁衣已經裹在女子身上,一個婆子居然還拿了脂粉來,在女子臉上胡撲了一氣,最後又拿了塊布條,搓巴幾下,塞進女人嘴裡。
折騰好半天,錢婆婆將被反捆了雙手的女子推倒在床上,吐了口氣,道:
「將她弄出角門,咱們的事兒便了結,回頭拿着賞銀,一塊吃酒去!」
一個婆婆嘿嘿笑,瞧着女子道:
「可惜這麼嬌嫩的,到了花舅爺手裡,遲早成殘花敗柳。」
「那是她自找的,當咱們那一位紙糊的不成,該她知道教訓,」
另一個婆子從鼻子裡哼了一聲:
「這平芷君自打被大爺帶回府上,就跟三夫人懟着干,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成天盤算要爬到三夫人頭上,等着吧,日後便是不死,也是進煙花柳巷的命!」
女子心下一寒,眼睛使勁閉了閉。
床上女子早沒了力氣掙扎,頭埋在那床破絮中,苦澀地笑了,原來她叫平芷君,還真是個高傲的,跟什麼三夫人爭寵,結果,眼瞧着便要落到一個爛人手裡。
平芷君幾乎是被拖出了歲蕪院,婆子們倒是沒綁她的腿,只一路連推帶踹地往前走。
穿過不知幾道小門,錢婆子瞧着前頭一個巷口,大鬆了一口氣,笑道:「咱們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算是圓滿了。」
平芷君卻灰了心,猜出到了角門,此時要被人扔出去,可不是這輩子便徹底糟蹋!
腳一軟,平芷君差點要栽到地上。
拐過巷子時,平芷君已經是被人拖着在地上走,青石板路一棱一棱,磨得她膝蓋生疼。
「大白天的,你們要去哪兒?」有人突然擋住了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