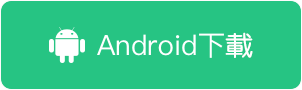三娘是我們這塊的叫法,在別的地方也叫三伯母。
「三娘,你這是咋了?」我跑出去問。
她用袖子抹了把眼睛,說:「我最近總感覺有人跟着我。」
我和爺爺對視一眼,都不大明白有人跟着她,她來我家幹啥。
沒等我問,三娘就接着說:「這些天一到晚上我就聽見有人衝着我喊媽,聲音有氣無力的,聽的人心裡難受,我是一宿一宿的不敢睡覺,實在是熬不住了。」
我遲疑道:「三娘,你是不是想孩子想多了,聽岔了?」
三娘今年三十多歲,一直想要孩子,大醫院也去了好幾家,欠下一屁股債,治了五六年也沒能懷上。
不過幾個月來她倒是沒再去醫院,一直在村里種地。
她緊張的說:「我沒聽岔,你三大爺也能聽見,。」
爺爺盯着她,半晌不說話。
三娘臉色漲紅,看着有些心虛:「叔,你這麼看我幹啥?」
爺爺問:「你們這幾個月是不是找看事的人了?」
三娘垂下頭,支吾好半天才說:「在縣城找了個專門看生子的靈婆,都說她生子方面找她很管用,我們就去看了兩回。」
爺爺沉下臉,說:「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你們兩個生不出孩子是身體的問題,得好好去看醫生,想這些歪門邪道的沒用。」
三娘哭着說:「我也想去看,可實在是沒錢了,我每天吃藥,還往肚子扎了好幾針,欠那麼多債,日子都要過不下去了哪還有錢去看醫生?看一次靈婆才五十塊錢,我就是想要有個念想。」
看着三娘哭,我也忍不住紅了眼眶,連忙給她遞紙。
三娘跟我三大爺本來家裡日子不錯,兩個人雖然沒有大本事,但都是吃苦認乾的人,在村里沒個孩子,總是被人指指點點,兩個人總是抬不起頭來,這才魔怔了似的非要生個孩子。
爺爺蹲在門口,掏出煙袋鍋子,吧唧幾口才說:「你先回去蒸一鍋二米飯,準備一葷二素的供品,我晚上就過去。」
三娘連聲應了,急忙走了。
「爺,我三娘這是咋了?」我擔憂道。
爺爺吐出口煙,「被纏上了,她找個那個靈婆有點本事,的確給她招了個願意投生的小鬼來,可你三娘生不出孩子是她身體的問題,跟你爸不一樣,那小鬼沒法投生,不願意離開,這才纏上你三娘。」
我納悶的的說:「爺,你咋知道的?」
他都沒細問我三娘,咋就知道是被要投生的小鬼纏上了?
爺爺回道:「從你三娘的面相上看出來的。」
這也行?
看我滿臉驚訝,爺爺接着說:「等這事解決了,我教你看面相。」
我忙不迭的點頭。
晚上,爺爺買了好幾沓之前,還有好些個金元寶這才帶着我往三娘家去。
路上,我問爺爺:「爺,三娘這次被纏上跟那討債的東西沒關係吧?」
「沒有。」爺爺解釋說:「這是兩碼事,討債的黃皮子活了不少年頭,不敢胡來,況且也就是今天來找我的是你三娘,實在親戚不好拒絕,要是旁人我早就推掉了。」
我心裡踏實了點,把昨天的夢說了一遍,「這會不會是那黃皮子特地來嚇唬我的?」
我知道自己現在有些草木皆兵了,可實在是心慌,畢竟黃皮子的下一目標不是我就是爺爺。
爺爺想了想,說:「沒準是,你別怕,爺爺不會讓你出事。」
「爺,你這些天關在屋子裡都在幹啥呢?」看爺爺精神不錯,我一股腦的把壓在心裡的事都問了出來。
他捶了捶腰,臉上有了笑容,臉上的褶子更深,「我在準備對付那黃皮子的東西,再過個十來天黃皮子還會找過來,到時候找機會把它給解決了,殺人償命,雖說它來找我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沒看見你結婚生子有出息,爺爺不想死。」
聽爺爺這麼說,我徹底放了心。
到了三娘家,爺爺立馬讓三娘盛一碗二米飯過來。
爺爺點上三個香,插在二米飯上,把碗放在門口左邊,跟三娘說:「你找個盆把那些紙錢和元寶燒一半,然後把紙灰碾碎,撒在門口。」
「哎。」三娘立刻去了,等三娘把灰撒好,爺爺就把窗戶都關上,讓三娘燒剩下的紙錢和元寶。
爺爺走到屋子中央,從兜里掏出來一張黃紙,上面用硃砂畫着副畫,勉強能看出來是個鳥身人頭的東西。
我心裡奇怪,爺爺怎麼會用這個了?別人看髒驅邪啥的不都是用符紙麼?
爺爺走到火盆邊上,盯着香燒出來的煙,我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發現那些煙往上升一段後竟然都朝着我這邊飄。
爺爺也看向我這邊,準確的來說是看向我身後的牆角,「走吧,你與這家無緣。」
我汗毛都豎起來了,僵着脖子不敢回頭。
說完話,爺爺就把那張紙扔進了火盆里。
三娘突然挺直身體,渾身發抖,顫着聲音說:「叔,他又在叫我。」
爺爺陰着臉,從兜里掏出來一枚木製的衣扣子,斥道:「我好生送你離開,莫要不識好歹。」
爺爺這話說的文縐縐的。
他這話剛說完,在門前的紙灰上就出現一雙小孩的腳印,腳尖朝着門外。
幾秒後,爺爺呼出口氣,跟着三娘把紙錢和元寶都燒完。
三娘扶着門框站起來,臉色發白,問爺爺:「叔,送走了?」
「嗯。」爺爺說:「實在沒錢去治病了,你就抱個孩子,養的好跟親的沒啥區別。」
在我們這有些人孩子生得多養不起就想找個靠譜的人家把孩子送過去,不為錢就是想讓孩子享福。
三娘低聲說:「我已經讓我娘家幫忙打聽了。」
從三娘家出來,我立馬問:「爺,你燒的那張黃紙上畫的是啥?還有那個衣扣子真那麼厲害嗎?」
爺爺罵道:「你個不識貨的,什麼衣扣子,那是雷劈桃木,辟邪的好東西,至於那張紙……」
他笑了起來,說:「等解決了黃皮子,我把我的本事都交給你,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我應道:「好,我一定好好學。」
一直懸在半空的心終於落到了實處,不再擔驚受怕,我以為自己終於能睡個好覺,誰知道剛關燈上炕就被人掐住腰,緊接着撞進冰涼的懷抱里。